胡爾夫:盡訴人生激盪起跌的馭火者
胡爾夫的一生,只為音樂而活、為音樂而狂。他的歌曲,有着輕鬆有趣的詼諧、成長掙扎的痛楚、愛情肉慾的感性和悲天憫人的愁鬱。他的歌曲,訴說着最真實的人生。

1879 年,布拉姆斯 (Johannes Brahms) 與胡爾夫第一次見面,並且為胡爾夫的音樂前途,給了好些意見。可是,不久的將來,年輕的胡爾夫,會成為大師的一位最敢言的批評者。
布拉姆斯面對胡爾夫層出不窮的劣評,不太上心。有一天,他在午餐聚會中打趣說:「今天是星期天,我得去買份《維也納沙龍報》,看看胡爾夫還有什麼好說。」

胡爾夫 (Hugo Wolf) 1860 年生於現今位於斯洛文尼亞 (Slovenia) 境內,舊稱為溫迪施格雷茨 (Windischgraz) 的小鎮。他的爸爸繼承了祖父的皮革生意,但本身卻是多才多藝,懂得鋼琴、小提琴、長笛甚至是結他。胡爾夫起初的音樂教育,就是來自父親;加上另外弟弟以及叔父,他們可以組成一個小室樂隊,在閒時演舞曲娛樂。
八歲時,他第一次看了意大利歌劇,從此對歌劇甚至音樂都極為投入。他把羅西尼、唐尼采第等等歌劇作曲家的作品彈得滾瓜爛熟,還研讀了海頓、莫扎特與貝多芬的交響曲。除了音樂以外,他把其他學科全都荒廢掉。
胡爾夫的爸爸雖然熱愛音樂,卻不認為音樂能成為一份職業,只能夠當業餘的興趣。但是,胡爾夫矢志不二,千方百計要走音樂的路。他在十五歲時,寫成了兩部大型的鋼琴作品,題獻予父親,作為證明自己音樂才華的證據。
於是,在 1875 年,他前往了維也納,踏上了音樂這條不歸路。

在繁華的維也納,胡爾夫可以貪婪地看歌劇。而且,維也納也招來了不少有才華的音樂學生,在音樂學院進修。胡爾夫的同班同學之一,就是與他同年出生的馬勒 (Gustav Mahler)。
入讀音樂學院的第一年,正好華格納 (Richard Wagner) 到訪維也納,並且準備在 11 月上演《唐懷瑟》 (Tannhäuser) 與《羅恩格林》(Lohengrin)。胡爾夫全都沒有錯過,而且立時被這位「大師中的大師」迷倒:他偷偷地走進皇家歌劇院 (Hofoper) 聽華格納下午綵排,然後觀看正式演出。他被《唐懷瑟》的音樂震懾:「序曲是何等地美妙,然後就是歌劇正式開始——我完全沒法用言語形容!」
華格納歌劇中新穎的聲音,加上具英雄色彩的故事,令胡爾夫感到,華格納正是音樂的未來。他將華格納奉為偶像,在歌劇院後台出沒、在華格納下榻的酒店徘徊,他甚至混熟了酒店工作的人員,為的是希望能見華格納一面。
終於,有一天他在酒店的走廊中,與華格納交談。他向他的偶像說,多麼希望華格納為他的作品給點意見。但在那怪異的場合,華格納托辭說趕時間,就連堆着的書信,也沒有時間回覆。不過,他卻說了幾句對胡爾夫而言,甚為有影響力的說話:「我像你那個年紀的時候,別人看我的作品,沒有人會曉得我能在音樂的世界中走多遠。」然後他說:「等到你更成熟時,寫了更好的作品,而我又來維也納的時候,帶你的作品來給我看。」最後,他說句要努力學習,就離開了胡爾夫。
對十五歲的胡爾夫,這就是為他一生訂立了方向。
可是,生性反叛的胡爾夫,不多久後就被音樂學院勒令停學。在學業上,他走着完全離經叛道的路,要在音樂上不受束縛,認為學院制度專制與課程內容保守,對他尋找在創作上尋找自己的聲音毫無幫助。而學校將他停學,因為他的紀律有相當嚴重的問題。
中止學業,胡爾夫只能返家;但回到鄉間,又沒有了接觸音樂的機會。於是,他嘗試在維也納投靠朋友,以教學為生。他脾氣暴燥,而且情緒亦大起大落,但是因着他音樂的才華,讓他建立起一班朋友和支持者。
1883 年,華格納逝世。胡爾夫的偶像,再沒有為他的音樂下評語,也沒有為胡爾夫的將來指引什麼路向。他雖然創作了好幾首精細的歌曲,但是他感到自己活在巨人的陰影下。「我還可以做什麼?他沒有為我留下空間,就像一株宏偉的樹張開繁密的樹幹,留下陰影。」
之後的幾年,他沒有太多創作。反而,因着友人的介紹,他得到了一份樂評人的工作。友人梅蘭妮 (Melanie Köchert) 的丈夫,是維也納宮廷的寶石匠,在其引線下,胡爾夫在《維也納沙龍報》(Wiener Salonblatt) 開始寫起樂評來。他在報章中言辭狠辣,認為華格納的路線,是具前瞻性的出路,而對布拉姆斯為首的保守,大肆抨擊。
「布拉姆斯的交響曲,某程度上是合格與有優點的作品;可是,作為『貝多芬繼承者』的交響曲,這卻是完全失敗之作,因為布拉姆斯欠缺了『貝多芬繼承者』所必需的特質——原創性。」胡爾夫如此形容當時已是維也納最重要的作曲家,當然招惹不少敵人。
我們從胡爾夫大量的樂評文章中,窺見了他對音樂的期許。他認為一首真誠的音樂作品,容不下空泛、虛無與偽善。他批評得最徹底的,就是脫離文字、將交響曲奉為絕對的音樂。
他也為自己帶來新的稱號:他是一頭不折不扣的「野狼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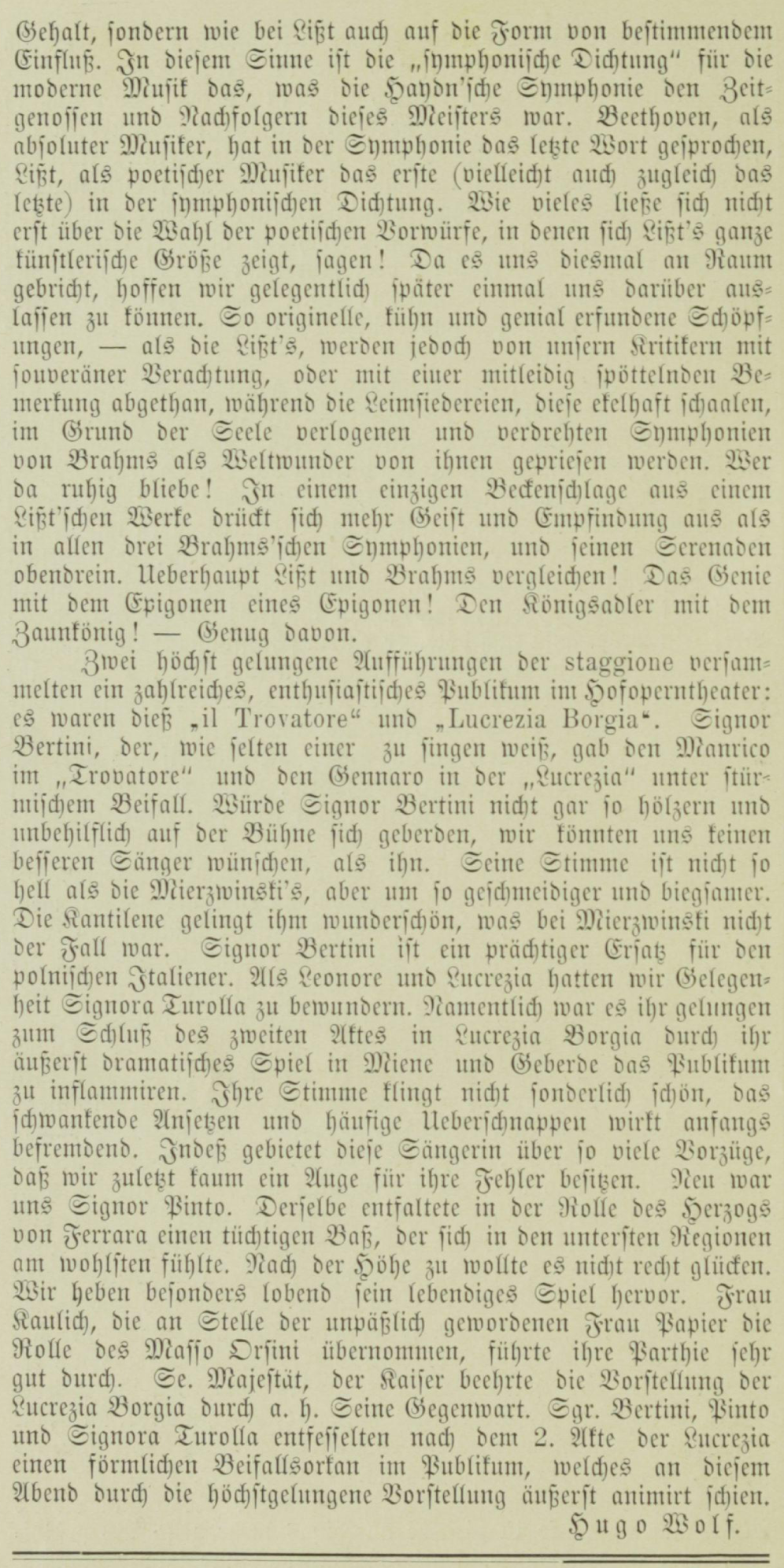
1888 年,胡爾夫終於迎來了真正的創作高峰。他開始為詩人莫里克 (Eduard Mörike) 譜曲,靈感一發不可收拾,短短的幾個月,就創作了四十多首。他由早工作到晚,形容有「一千匹馬力」的能量。而且,他發現這些都不再是年輕的作品。「我是為永恆而寫;這些都是大作」他如此形容。
胡爾夫在自己友人的圈子中有着不少支持,立即分享這些新作。而這位號稱「野狼」的樂評人,音樂雖然為人欣賞稱讚,但是他狠辣批評維也納一眾作曲家的過去,沒有被忘掉。胡爾夫雖然已經精於創作歌曲,除了和聲大膽新穎外,音樂帶出詩歌的層層未言明之感情,更是有效直接。可是,他沒有忘懷偉大的華格納,着他創作更偉大的作品。而對胡爾夫而言,那就是管弦樂的大作。
受着李斯特的鼓勵,胡爾夫寫了以希臘神話為題的交響詩《潘賽西莉亞》(Penthesilea)。可是,當他把樂曲交至維也納愛樂樂團安排首演時,卻被樂手取笑:「還是把它留在歌劇院給看守的人留着好了。」被他狠狠批評過的人,一一都跑出來取笑他,認為那斗膽批評布拉姆斯的樂評人,還只是這樣水平的作曲家。
而對於胡爾夫而言,最重要的,卻是要像華格納一樣,創作歌劇。可是,他要在他最後崩潰前的不久,才把一部歌劇完成。
胡爾夫一時間有着「一千匹」的創作動力,然後完成大量深刻的作品。可是,當他憂鬱的時候,卻可以幾年間毫無作品。
他大起大落的情緒,幾乎是在一開始就為人認識。胡爾夫的一位學生,曾經回憶起一個夢境:歌劇院演華格納的歌劇,眾人都在吃喝,遠處的一坐高塔,是歌劇的指揮。歌劇的指揮,正是從那高塔中指揮着樂團,但是高塔卻被鐵欄重重包圍。夢境中的音樂家,像頭野獸般暴燥。
這段出現在心理分析家佛洛依德 (Sigimund Freud) 的大作《夢的解說》 (Die Traumdeutung) 的一個夢境,正要預示着胡爾夫的命運。學生與現實中身為音樂老師的胡爾夫,有着好感;因此,佛洛依德在演繹着夢境中,直接指出夢中的音樂家,就是那位老師。而夢中的高塔,彷彿就是老師在學生心中的地位與成就;可是鐵欄的外圍,令音樂家在內像是野獸般被關着,最終要令他瘋掉。
在佛洛依德下筆寫《夢的解說》差不多同時,胡爾夫也在寫他一生唯一能完成的歌劇《科羅希多》(Der Corregidor)。起初他認為這個劇本一文不值,但 1895 年間,他忽然「像着了瘋」般工作。歌劇建基於一段疑似的偷情,現實中的胡爾夫,卻是與一名有夫之婦相戀:梅蘭尼與胡爾夫的戀情,在 1893 年被揭發,可是之後卻仍沒有中止;梅蘭尼的丈夫,依然支持着胡爾夫的工作,而梅蘭尼則陪伴胡爾夫,直至他去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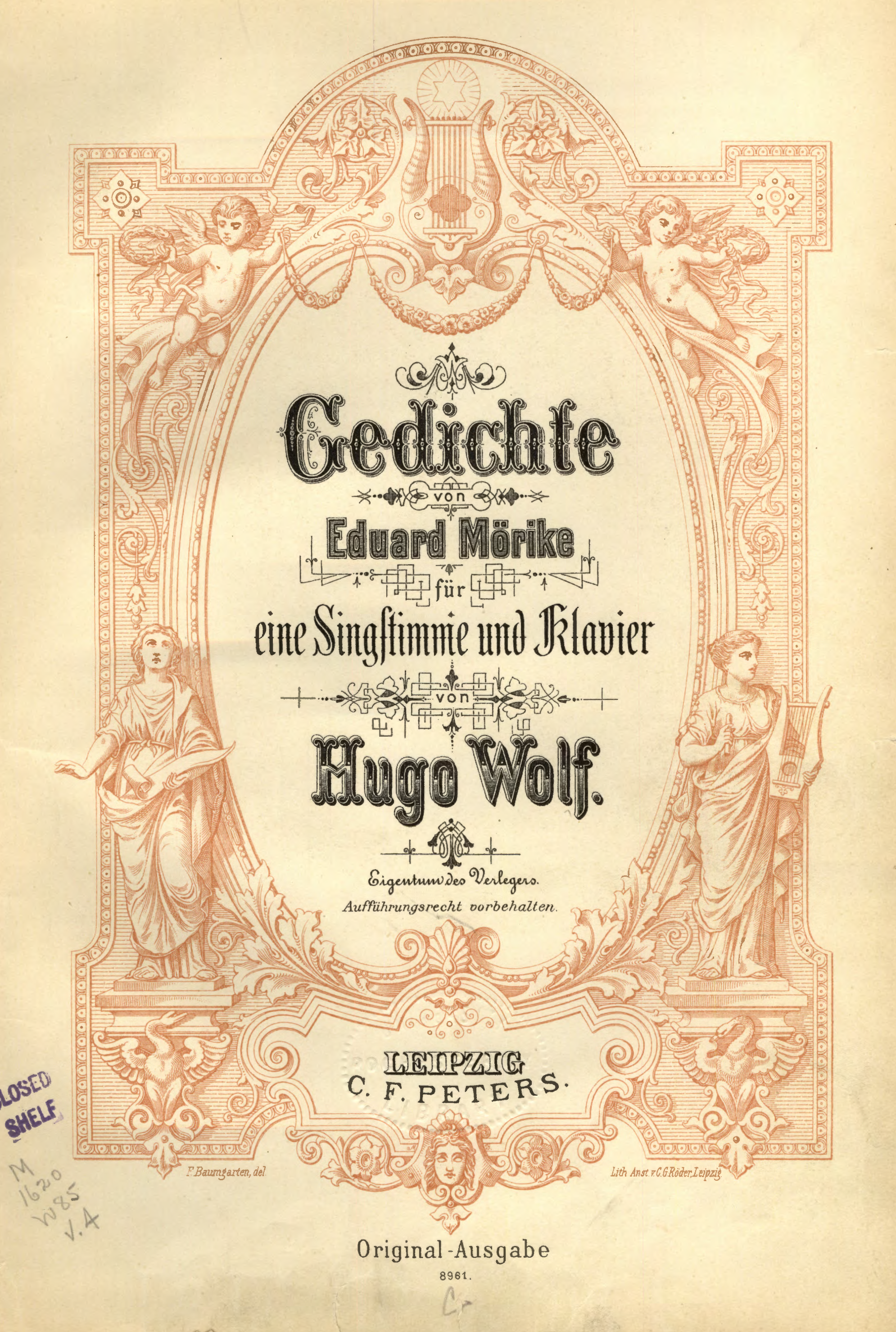
1896 年,《科羅希多》首演,但只能演出一場。不久之後,胡爾夫終於要面對命運。
年輕時,胡爾夫因着友人慫恿一夜風流,過後卻染上梅毒。步舒曼的後塵,梅毒在他身上蟄伏廿年,終於在 1897 年完全破壞了神經系統。新任被委為維也納宮廷歌劇院音樂總監的馬勒,本來應允了兒時同窗胡爾夫上演他的《科羅希多》,怎料臨時改變主意。胡爾夫在眾人面前發狂,彈着自己的音樂,並且宣佈「解僱」了馬勒,自己「擔任」宮廷歌劇院的音樂總監。
圍觀而震驚的友人,只好將失常的胡爾夫,送往精神病院。他一生的情緒波動、對噪音的敏感、常怕被人毒害的擔憂,除了是胡爾夫本身的怪脾氣以外,也因着病毒逐漸破壞神經系統所致。1897 年後,胡爾夫再不能寫作。
往後幾年,胡爾夫的病情時好時壞,梅蘭尼每星期會探望幾次,就像克拉拉探望進了精神病院的舒曼一樣。可是,因着梅毒帶來的精神病,是不會逆轉。胡爾夫最後在 1903 年去世,終年只有 42 歲。深愛着他的梅蘭尼,活在憂鬱與自責中,在胡爾夫離世後三年,她在維也納的家中由四樓墮下,了結生命。
胡爾夫的一生,只為音樂而活、為音樂而狂。他的歌曲,有着輕鬆有趣的詼諧、成長掙扎的痛楚、愛情肉慾的感性和悲天憫人的愁鬱。他的歌曲,訴說着最真實的人生。
他一生最鍾愛的一首作品,名為《馭火者》(Feuerreiter)。詩歌中的騎士,面對被烈火吞噬的磨坊,駒馬直前;在如地獄一般的火場中,他是不是神的使者?可是,人們在燒完了的火場找到的,是騎士依然坐着馬,只是已成白骨。最後,呼的一聲,白骨盡化成灰。
在瘋狂的鋼琴聲、聲嘶的旋律中,胡爾夫寫下了最能觸動神經的音樂。他曾說過,如果他不能創作,他一生就毫無用處,乾脆掉進糞堆就好。
短暫一生過後,他被人葬在維也納的中央墓園,與舒伯特和貝多芬為鄰。
此文章為 「音樂遊蹤」講座系列:奧地利站 之專題文章。講座日期為 2018 年 6 月 6 日。


